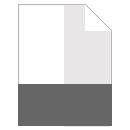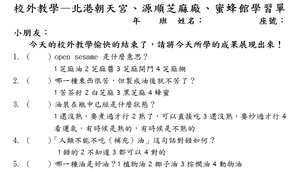:::


胡適,原名洪騂,安徽績溪人,後取自《天演論》的「適者生存」之義,改名適,字適之。幼時接受家塾式的傳統教育,接觸過許多白話文的舊式小說和傳奇。1904年赴上海,就讀於新式學校,閱讀了不少梁啟超的文章和嚴復的翻譯書籍。15歲時,即為文闡述中國富強之道唯有遵行「物競天擇,適者生存」之理,力主學西方之長,來補中國所短。1906年,進入中國公學,在校編辦《競業旬報》,發表大量的白話文章。1910年,考取庚子賠款第二期官費生,赴美國康乃爾大學農學院留學,後轉讀文學院。1915年,再轉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,師於杜威,深受其實用主義的影響。1917年,取得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,隨即返回中國,任教於北大,並投入《新青年》的編輯。1938至1942年,胡適被派任為駐美大使,1946至1947年回國就任北大校長。1949年滯居紐約,1958年來到台灣,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,1962年2月24日下午六時,在歡迎新院士酒會結束時,因心臟病猝發去世。 胡適一生的著作豐富,包括《中國哲學史大綱》(上卷)、《胡適文存》四集十二卷、《戴東原的哲學》、《白話文學史》(上卷)、《四十自述》、《水經注版本四十種展覽目錄》等 。在美留學時,胡適曾明確表達他對文學的看法:「文學在今日不為少數人之私產,而當以能普及最大多數之國人為一大能事。」胡適堅信文化的真正創造者是民眾,而非少數的上層菁英,由少數人定義出的民族文化模式是荒謬的。他強調文化就是要反映出多數人民的生活,文學必須照顧到社會大眾,而不是追求菁英獨享的精緻嗜好或寄興言志的艱澀文句。就胡適而言,「語言是思想表達最重要的工具;一國之語言有如重大而根本之變化,則其社會和思想生活,也必有極大改變。」1917年1月,他在《新青年》發表著名的〈文學改良芻議〉,提倡以白話文取代文言寫作,目的就是為了造就大眾的文學,促使教育的普及和思想的改革。1918年4月,胡適再發表了〈建設的文學革命論〉,呼籲新文學要以社會問題為創作的中心題材:「如今日的貧民社會,如工廠之男女工人、人力車夫、內地農家、各處大負販及小店舖,一切痛苦情形……並且今日新舊文明相接觸,一切家庭慘變、婚姻苦痛、女子之位置、教育之不適定……種種問題,都可供文學的材料。」1918年6月,《新青年》以「易卜生專號」出刊,刊載了胡適的〈易卜生主義〉。在胡適的眼中,易卜生主要致力於批判家庭、法律、宗教、道德中的陳腐和舊習的詐偽,他特別推崇易卜生對社會壓抑個性和虛偽醜惡的抨擊。「易卜生的文學,易卜生的人生觀,只是一個寫實主義。」而這種寫實主義,正是胡適認為可以用來改良社會的重要憑藉。胡適認為要解決中國問題,要有比建軍等更為深刻的措施,他在1915年2月21日的日記裏曾經提到:「國無海軍,不足恥也。國無陸軍,不足恥也。國無大學、無公共藏書樓、無博物院、無美術館,乃可恥耳。」他主張教育才是建立新中國的基礎。當1919年5月「五四運動」發生時,胡適人在上海,迎接來華講學的杜威。他對北京學生遊行一事頗不以為然。他強調學生職責是讀書,應以「讀書救國」、「教育救國」,透過新文化來改造落後的國民性,至於政治救亡的工作,則是政府該盡的責任。1919年7月,他於《每週評論》31期發表〈多研究些問題,少談些主義〉一文,李大釗隨之發文〈再論問題與主義〉表示不認同,挑起了所謂的「問題與主義之爭」,這被視為是新文化運動陣營中,改良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兩派的論戰。在五四激情的當下,胡適的溫和救國主張受到不少的批評,不過隨著情勢逐漸緩和之際,他的看法卻開始獲得迴響,加上他早期在新文化運動上建立了崇高的聲望,因此,雖然他本人並未參與或指揮實際的遊行活動,但也被視為是五四運動的半個精神領袖。在東西文化論戰時期,胡適認為傳統文化已經無法適應新時代的挑戰,因此對於西方文化不該拒絕,也不能選擇性的折衷吸收,反而要全心全意地歡迎和接受。他首度在英文論文《今日的文化衝突》中使用了「全盤西化」的字眼,後來陳序經承接了這個說法。不過,「全盤西化」是摒棄一切的傳統文化嗎?事實上,胡適不擔心中國人會失掉自己優秀的傳統。他認為舊文化中真正有價值的,能帶給人民精神力量的東西是不會喪失的;反之,若因擔心失去傳統,在西方文化的挑戰面前,瑟縮不前,反而喪失文化更新與現代化的契機。胡適和傳統文化的衛道之士們相比,顯然對於中國文化的信心要強得多。胡適早在留學時期,就力求借鑒西方的新思想、新方法,來重新研究中國文化遺產。他在博士論文《先秦名學史》的導論中提到:「怎樣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現代文化,使它能同我們的固有文化相一致,協調和繼續發展……唯有依靠新中國知識界領導人物的遠見和歷史連續性的意識,依靠他們的機智和技巧,能夠成功地把現代文化的精華與中國自己的文化精華聯結起來。」五四運動後,他發表〈新思潮的意義〉,宣示「研究問題,輸入學理,整理國故,再造文明」。他重建了中國哲學史、文學史;提倡女子教育、普及教育,提出高等教育;也倡導改造民俗禮儀,建立新道德。綜合而論,大至治國大計,小至繪畫技巧,胡適始終本著中西結合的原則來從事改革與創新。胡適加入《新青年》編輯時,曾有「二十年不談政治」的要求,表達過不贊成激烈的「五四運動」,加上強調以文化救國等溫和主張,因此,胡適常被歸類為與現實政治保持距離的知識分子代表之一。然而當1919年、1920年間,周作人、魯迅、等人大力鼓吹日本新村運動,主張要遺世而獨立,過一種自給自足的烏托邦生活,胡適卻深不以為然。1920年4月,他在《新潮》2卷3期以〈非個人主義新生活〉為題,力斥遁世主義之不足學習,強調個人仍然應該以服務社會為己任。對於混亂動盪的政局,胡適究竟如何抉擇?或許從他的〈易卜生主義〉中可推敲出一些端倪。胡適闡論易卜生的「世上最強有力的人就是那個最孤立的人!」時說:「……孟軻說『窮則獨善其身』,這便是易卜生所說『救出自己』的意思。這種『為我主義』其實是最有價值的利人主義。所以易卜生說:『你要想有益於社會,最妙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。』」周明之在〈胡適與文學革命-中國近代知識份子的疏離感和抗議〉中說,胡適唯一可行便是成為易卜生式的寫實自然主義者,「掙扎悲觀和樂觀之間」,只有在「救出自己」的心情之下,才能做到利人主義,他才能成為「世上最強有力的人」,不過同時也成為了「那個最孤立的人」。
資訊
素材
創用CC 姓名標示-非商業性-相同方式分享 2.0 台灣
2010-05-28
教學資源檔案連結
his_00001425.zip (36.98KB)
資源評論或心得分享
相關資源